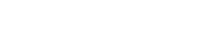本文转自:上游新闻

文章图片
布谷声声苞谷香
唐富斌
走 , 回老家黑山吃嫩苞谷去 。 即刻 , 那种清香、回甜的味道就会在舌尖上荡漾起来 。
“苞谷——苞谷——” , 布谷鸟(民间称苞谷雀)以她那浑厚、圆润的中音歌喉 , 吟唱着复调式的摇篮曲 , 从春播开始 , 不舍昼夜 , 一路陪伴着苞谷种出苗、拔节、开花、身背苞谷娃娃、灌浆、乳熟、蜡熟 , 直到完全成熟 。
李时珍《本草纲目》里的苞谷称玉蜀黍 , 名字也很是美味的 。 但要说吃味我偏爱嫩苞谷 。 不过要吃上可口的嫩苞谷 , 时机的把握很关键 , 一般选择乳熟期至蜡熟期之间掰取为佳 , 即以苞谷须为淡黄绿偏淡棕色为宜 。 否则 , 靠前掰取的籽嫩如水 , 乳臭味干 , 若是水煮苞谷棒子啃起来更没感觉;靠后掰取的呢 , 籽籽又显得稍硬了些 , 老噗噗的 , 调动不了味蕾的灵性 。
巴渝海拔200多米的平坝乡村 , 吃嫩苞谷大都在小满至芒种这段时间 , 我老家地处海拔600多米的山区 , 尝鲜正是当下农历六月这个时候 。
童年的肚子经常饿得“咕咕咕”闹意见 , 因此 , 从鹅黄的苞谷苗颤微微破土的那一刻起 , 我的眼睛就像露珠挂在了她的叶尖上 , 恨不得看到她马上背上可爱的苞谷娃娃 。
那年月 , 吃的首要任务是为了填饱肚子 , 因此嫩苞谷的吃法就显得有些粗陋 , 今天看来却是好事 , 好就好在于它保持了食物原始、生态、本味的特色 , 至今都令人念念不忘回归生命的原乡 , 找寻、品尝那清淳的滋味 。
火烧苞谷棒子 , 想来是燧人氏钻燧取火、苞谷西传入华以来就有的一种古老吃法 , 后来演变成了乡下人闲适的吃玩 。
物质匮乏的年代 , 山里的苞谷不说容易受到饥饿的人们偷盗 , 就是野猪见了也会馋得两眼放光 。 为了守护苞谷地 , 一次我跟班堂大哥来到了寂无人居的猫岩三堂塆 。 那是一个夜晚 , 气象呈现为月黑头 , 即伸手不见五指、抬头不见月牙 , 且是大雾锁空山 。 人字形的草棚下 , 只见大哥将一杆弯把手火药枪挂在壁上 , 然后在门口用木柴升起一堆熊熊的烟火 。 为了表明苞谷地有人看守 , 我们时不时对着静默的山野或高声大气的说话 , 或“喔——喔——”大吼 , 大山似乎也心领神会 , 总以其默契的回声穿过夜空和迷雾 , 与我们一起宣示着勿容侵犯的强大存在;同时 , 也没有忘记顺手从旁边的地里掰取新鲜苞谷 , 在火上烧烤着打牙祭 。
柴火烧苞谷 , 烧到八九分 , 面色微黄有丁点焦糊即可 , 当然面上还须沾上少许的柴灰 , 否则吃起来就总觉得少了点莫名的味 。 那天晚上 , 火光映衬下的我捧着苞谷棒子狼吞虎咽 , 吃得野性 , 吃得嘴角传香、心窝溢甜 。 事后 , 由于沾满碳灰的小手不注意在身上东一摸西一揩 , 使自己的小脸蛋活脱脱成了一幅川剧大花脸 。 大哥看了我的样儿“咯咯”直发笑 。 我估计 , 野兽见了这幅比它还野性的形象也会畏惧得打退堂鼓的 。
另一种传统吃法是水煮苞谷棒子 。 不少地方的苞谷棒子无非是裸煮 , 我恰好推崇老家的做法:除了苞谷要杆上刚刚掰取的 , 根蒂还在渗出晶莹的汁液那种外 , 不得去包衣(外壳)、去谷须 , 且煮时不宜将锅盖捂死 , 让苞谷在蒸气自由散发的过程中接受舒畅的蒸煮 , 如此到其熟时包衣也始终保持原来的绿色 , 颗粒始终呈现乳白色或乳黄色 。 这样的水煮苞谷 , 既有本来的可人品相 , 又有原生的清香回甜味 。 同时 , 剩下的煮苞谷水也不会任意抛洒一滴 , 而是在饭后的闲暇、谈笑中 , 作为你一碗、我一盅饭后打口渴的饮料 。 长大后多识了几个字才知道 , 这汪看似平淡无奇的嫩苞谷水 , 却蕴藏了中医健脾养胃、利尿消肿、清湿热、补五脏的秘谛 。 当然 , 我们过去并不晓得有这些好处 , 只是凭着感觉吃起舒服就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