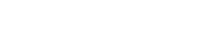本文转自:北京晚报
▌付振强

文章图片
插图王金辉
秋风响 , 蟹脚痒;菊花黄 , 品蟹忙……
当农历九月的刘海儿刚被秋风吹起一角 , 街上便开始有了螃蟹的气味 。 闲了大半年的大闸蟹专营店开始有了响动 , 探亲访友的车上除了满载的瓜果梨桃外 , 通常还要拎上一副草编的蟹篓 。 昔日占据餐桌霸主地位的鸡鸭鱼肉此时也纷纷让出了C位 , 一只只顶盖肥的螃蟹当仁不让地成了今天的主角 。 看着它刚刚还张牙舞爪转眼就蟹黄溢出了蟹壳 , 红光满面地成了盘中的“座上宾” , 人们的笑容里充满了喜庆和富足 。
眼下 , 正是河蟹大量上市的时候 。 别看螃蟹外表狰狞可怖 , 却是柴门小院饭桌上不可缺少的一道美味 。 螃蟹喜阴 , 河湖港汊、稻田、芦苇荡都是它的寄居之地 。 江浙一带有阳澄湖的大闸蟹声名显赫 , 华北明珠白洋淀的清水蟹同样远近闻名;北京的皇家园林颐和园 , 前些年也曾在接近西堤的湖面上 , 就着一片芦苇荷叶养起了河蟹 。 后来可能是和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号不符 , 才主动和螃蟹说了拜拜 。 机场路附近以前还有个与蟹文化有关的蟹岛度假村 , 有一年秋天去那里钓鱼 , 就见旁边垂柳依依的池子里不时有铜钱儿大小的螃蟹大摇大摆地爬上岸来 , 大人孩子见了都觉得既新奇又好玩 。
说来好笑 , 螃蟹不仅是一道美食 , 它那张青色的小背壳上还承载了不少故事 。 螃蟹面目狰狞 , 生性横行霸道 , 估计在成为美食之前 , 是没有多少人敢去碰它的 。 那么是谁第一个发现这道人间美味的呢?现已无据可考 , 但若把这个人奉为勇士 , 恐怕是不会有人反对的 。 所以后人常把那些勇于探索敢于尝试的人比喻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 赞誉他们是敢为天下先的勇士 。
不知从何起 , 螃蟹开始进入灰色地带里的快车道 , 成了人们兜转关系的媒介 。 礼品蟹、螃蟹券花样繁多 , 价码更是打着滚儿地往上翻 , 三两千元一盒的天价蟹并不稀奇 , 买主儿不少 , 但估计不全是自己享用 。 近年十一我去市场买蟹 , 往年红火的天价蟹没有了 , 用来压分量的草绳蟹也不见了踪影 , 取而代之的是个头不小的螃蟹十几块钱一只 , 明码标价 , 任意挑选 。 相信随着正风肃纪的深入 , 螃蟹迟早也会回到它的本来面目 。
吃螃蟹的最好季节应该是每年的“十一”前后 , 这个时候的螃蟹膏满肉鲜 , 味道最佳 。 北京人嘴刁 , 吃蟹只选这个时候 , 过了季节的螃蟹 , 看都懒得看一眼 , 只一句“空 , 没肉儿”就打发了 。 他们吃螃蟹喜欢先温一壶老酒 , 就着灯影浅斟慢酌 , 拆蟹的动作也从容不迫 , 先蟹腿 , 再蟹壳 , 最精华的肚腹部分要留到最后才剥开 。 蟹黄露出来了 , 嚼起来口感沙沙的 , 蟹膏吃起来则“咯吱咯吱”地有嚼劲儿 , 送进嘴里并不着急咽 , 静静等着那一疙瘩蟹香在口中慢慢舒展蔓延 。 拆下来的蟹壳蟹腿也不丢弃 , 而是摊在桌上饶有兴致地再拼搭出一副螃蟹架来 , 等滋味咂摸够了 , 酒盅往桌上“啪”地一扣 , 一顿螃蟹美餐才算画上句号 。
挑选螃蟹需要一点学问 。 民间有“九月团脐十月尖”的说法 , 意思是说农历的九月要吃母蟹 , 而进入十月 , 尖脐的公蟹正好膏满肉肥 , 有经验的食客就转而选公蟹了 。 好的螃蟹应该“青背、白肚、金爪、黄毛” , 凑近 , 还能闻到一股淡淡的土腥味 。 这是螃蟹独有的气味 , 是一种来自田野水塘温润潮湿的自然气息 , 说明螃蟹出生地的水质上乘优良 。 有人说挑蟹先要看它的尾部是否饱满凸起 , 其实大可不必直接上手 , 这个月份的螃蟹基本都饱满有肉 , 看看就可以 , 真捏疼了让它夹你一下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 挑蟹记住三点即可 , 一看螃蟹吐不吐沫儿 , 吐沫儿多的说明离水时间不长 , 新鲜;二是挑逗它时如果对你张牙舞爪 , 说明欢实儿 , 生命力强 , 多是刚捕捞上岸的;三是掀翻它时若能迅速翻转过来 , 说明体格健壮 , 直接抓了交钱走人 。
- 如果再来一次,万圣公主还会嫁给九头虫么?孙悟空一句话说出真相
- 甲状腺结节小,不用去管?医生表示:这句话不听,查了等于白查…
- 鼓励孩子时,这 3 句话别轻易说,会让娃更不自信
- 关羽的后代,向皇帝推荐了1个武将,上了战场这个武将却闹出笑话
- 刘伯温临死前对二个儿子说的一番话,竟然在200年后应验
- 11月22日小雪,老话“寒冬吃一宝,不把医生找”,“1宝”指啥?
- 晚上起夜与不起夜的人,哪个身体更健康?医生说出了实话
- 【医文医话】皮肤科:老年皮肤瘙痒症知多少?瘙痒不是“病”,痒起来真要命
- 肿瘤|为什么很多患者“宁死不放疗”?实话实说:4种癌症选放疗或更好
- 俗话说“立冬吃冬枣,一年不变老!”,吃了半个月,我终于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