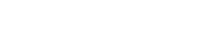回顾2021,展望2022,范建高教授全面盘点脂肪肝相关肝癌领域研究进展( 二 )
来自亚洲的数据显示 , NAFLD患者肝病负担及其相关肝硬化和HCC亦在不断增多 , 但鲜见我国NAFLD相关HCC流行病学数据 。
埃斯特斯(Estes)等基于肥胖和糖尿病的发病趋势 , 采用动态Markov模型预测美国NAFLD相关HCC年发病人数将从2015年的5160例增加到2030年的12240例 , 增长幅度达137% 。 该团队通过此模型预测 , 2016—2030年 , 中国、日本、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等其他国家NAFLD相关HCC患者数量将增加47%~130% 。
NASH是全球上升速度最快的引起HCC的慢性肝病 , 2030年全球NASH相关HCC发病率将比2015年大约增加150% 。 当前HBV和HCV相关HCC占比中下降趋势 , 预计到2030年NAFLD相关HCC将成为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HCC的主要病因 , 这在女性患者中尤其明显 。
临床特征和危险因素
尽管大多数HCC都发生在肝硬化基础上 , 但部分没有肝硬化的慢性肝病患者也会发生HCC 。 美国多中心研究报告显示 , 在2000年至2014年期间 , 12%(605/5144)的HCC发生在没有肝硬化的慢性肝病患者 , 而在NAFLD中非肝硬化HCC比例大于肝硬化相关HCC(26.3%比13.4%) , NAFLD是非肝硬化患者HCC最常见的病因 。 在NASH相关HCC患者中 , 没有肝硬化的比例高达20%~50% , 而在丙型肝炎等其他慢性肝病患者中该比例在10%以下 。 NAFLD相关HCC患者就诊时年龄比其他原因HCC患者大5~10岁以上 , 好发于65岁以上老年人 , 常合并心血管代谢疾病及并发症 , 而其HCC往往在更晚期才被确诊 。 在调整HCC分期、肝纤维化分期、年龄和潜在共病等影响因素后 , NAFLD相关HCC是否比其他病因导致的HCC更严重仍有待确定 。
男性、高龄、西班牙裔种族、吸烟、饮酒、肝硬化等是各种慢性肝病患者发生HCC的共同危险因素 。 对于NAFLD患者而言 , 吸烟、少量饮酒、肝纤维化等均是HCC发生的危险因素 , 其中肝纤维化分期是NAFLD患者总体生存时间和HCC风险最为重要的预测因素 。 NAFLD患者HCC发病风险随着肝纤维化进展 , 特别是肝硬化的发生和肝脏失代偿而不断增高 。 NAFLD患者肝病和全因死亡率都随着肝纤维化程度的加重而不断增高 。
众所周知 , 胰岛素抵抗和代谢功能障碍是NAFLD的重要发病机制 , 2020年国际专家小组提出将NAFLD更名为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病(metabolicdysfunctionassociatedfattyliverdisease,MAFLD) 。 超重或肥胖、2型糖尿病、代谢综合征是NAFLD及其相关HCC的独立危险因素 。 虽然肥胖会增加许多癌症的发病风险 , 但肥胖与HCC的联系最为密切 。
近期有研究报道 , 即使在不曾经历过肥胖阶段的瘦人NAFLD中 , 仍有可能并发HCC以及心血管事件 , 这些患者尽管体质指数正常 , 但可能存在腹型肥胖、肌少症性肥胖 , 其实影像学证实的脂肪肝比体质指数判断的肥胖更能预测代谢紊乱和肿瘤风险 。
与其他病因导致的肝硬化相比 , 2型糖尿病与NASH肝硬化患者HCC风险增加有更强的关联 。 在NAFLD和糖尿病患者中 , 有效的血糖控制(糖化血红蛋白下降)与HCC风险降低相关 。 可以降低2型糖尿病患者HCC风险的药物包括二甲双胍、阿司匹林和他汀类药物 , 而磺酰脲类药物和胰岛素的使用则有可能增加HCC发病风险 。
在NAFLD的发生发展过程中 , 肝细胞脂肪变相关脂毒性、氧化应激、代谢性炎症、肠道菌群紊乱和免疫监控功能受损、胆汁酸代谢异常等都可诱导肝细胞癌变 。 这些因素可以解释在无肝硬化甚至无NASH的情况下NAFLD与HCC之间的内在联系 。
包括PNPLA3、TM6SF2、GCKR和MBOAT等基因突变体的遗传多态性与NASH及其相关肝硬化和HCC风险增加都密切相关 , 而HSD17B13等基因多态性则与HCC风险降低相关 。 事实上 , 这些易感基因的遗传变异与胰岛素抵抗、酒精滥用、HBV和HCV感染等患者脂肪肝和HCC风险增加都相关 , 目前尚不清楚对NAFLD来说 , 这些变异增加癌变的风险是否高于其他慢性肝病 , 或者是否还存在其他基因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 。 遗传多态性改变仅占HCC风险的一小部分 , 将遗传变异或多基因风险评分与其他传统危险因素结合到风险预测模型中 , 仅可能部分改善其预测性能 。
- 相关|【中国实用外科杂志】肥胖代谢病合并甲状腺癌外科治疗中国专家共识(2021版)
- 医药|陕州区医疗保障局:对全区定点医药机构2021年度服务质量进行年终考核
- 2021年血糖标准已放宽,2022年还会继续吗?控糖3原则,时刻牢记
- 中心血站|湘潭市中心血站2021年献血者及直系亲属临床用血费用报销(含“医院直免”)情况公示
- 桡动脉|崇州市人民医院2021年质量持续改进(CQI)项目竞赛圆满落幕
- 好消息!我市已开始全面执行《2021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新增74种药品!新版药品目录落地盐城!
- 技术|神介骑士论坛第37期 精华回顾——复杂颅内动脉瘤的治疗策略
- 孕产妇|2021年青海“母亲健康快车”开展义诊咨询近3.5万人次
- 汇报会|品牌铸魂 勇毅前行——南宁市第三人民医院举行2021年度品牌科室建设成果汇报会
- 医疗|台州医院荣获“2021浙江省人民政府质量管理创新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