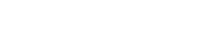IBD是一类病因尚不明确的慢性、特发性消化道疑难杂症,主要包括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Colitis,UC)和克罗恩病(Crohn’sDisease,CD)两种疾病表型 。 IBD具有无法治愈、病程反复、治疗困难、好发于青壮年的特点[3] 。 临床上,IBD病人普遍存在腹痛、腹泻、低烧、营养不良等症状 。 其中,UC病人会普遍出现脓血便和局限于结肠黏膜上层的炎症、溃疡等症状[4];而CD病人可在整个消化道范围内出现慢性炎症反应,表现出肠腔狭窄、瘘管、肠梗阻等疾病表现 。 此外,如果IBD病人不能实现有效的疾病控制,肠道癌变的风险将随着患病年限的推移而快速上升,最终将诱发小肠和结肠癌变[5] 。

文章图片
图1UC和CD的肠道表现
诱发IBD发病的四大因素:免疫、遗传、环境、微生物
目前,针对IBD的致病机制仍然没有统一的结论 。 免疫、遗传、环境、微生物被普遍认为是诱发IBD发病的四大因素 。
在基因层面,目前已经发现约250个基因位点与IBD有关,包括与上皮屏障、免疫反应、细胞自噬、细胞凋亡、氧化应激相关的基因[6] 。 这说明在IBD发病机制中存在基因与免疫系统以及肠道上皮之间的复杂关联 。
在免疫层面,IBD的慢性炎症反应与免疫系统的调节失衡和过度激活存在直接联系(图4) 。 一般认为,免疫系统的激活起始于结肠上皮的破损和外界抗原的入侵,最初会引起固有免疫的激活,树突细胞、巨噬细胞、嗜中性粒细胞等会参与到这个过程中 。 而随着免疫系统和消化道炎症的反复激活,最终将逐渐形成不可逆的慢性炎症,这主要与适应免疫的激活有关 。 其中,Th1和Th17细胞及其相关炎性因子的激活被认为与CD发病有关;而Th2和Th17细胞及其相关炎性因子的激活被认为与UC发病有关 。 此外,调节T细胞、固有淋巴细胞、B细胞等也参与到了IBD的免疫进程中[7] 。

文章图片
图2免疫系统在UC发病机制中的调控作用[7]
在环境层面,众多环境因素都与IBD的发病存在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图5) 。 城市化因素、空气污染、抗生素摄入、吸烟、消化道感染、日常饮食结构、精神压力等因素都会影响IBD的发病概率[8] 。

文章图片
图3影响UC发病的主要环境因素[8]
在微生物层面,肠道菌群是维护结肠上皮微环境稳态的重要因素 。 目前已有大量文献表明肠道菌群的紊乱会加速IBD的疾病进展 。 IBD病人的肠道菌群紊乱是肠道上皮微环境恶化的表现,主要表现在菌群多样性的下降、菌群结构性的改变和潜在致病菌含量的升高[9] 。 肠道菌群和宿主的互作也是导致IBD疾病进展的重要因素 。
综上所述,影响IBD发病的多种作用因素之间存在密切的相互关联 。 而这种复杂的多维度相互作用,最终形成了一个系统的IBD作用机制网络,这也给IBD发病机制的研究和临床治疗带来了巨大挑战 。
尚未明确的IBD致病因素导致两种治疗研究方向
1、复杂的药物疗法
复杂的发病因素和未知的致病机制很大程度上限制了IBD的治疗 。 临床上针对IBD的治疗主要分为药物疗法和手术疗法两类 。 在药物疗法中,对过度激活的免疫系统和炎症的抑制是药物的主要作用靶点 。 非甾体类抗炎药物(美沙拉嗪、奥沙拉嗪)、皮质类固醇(强的松、布地奈德)、免疫抑制剂(环孢素、甲氨蝶呤)、生物制剂(英夫利昔单抗、阿达木单抗)等都被广泛的应用于IBD的疾病治疗中[10] 。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还没有任何一款针对IBD治疗的特效药物,IBD的药物疗法普遍存在用药流程复杂、用药种类多等弊端 。
- 市三医院烧伤科入选“中国研究型医院评价遴选”研究型学科
- 叮~一份2022中医香疗研究院年度总结请查收
- 专家解读 | 山东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念明:实施种业振兴,突破种源卡脖子技术
- 肝癌|研究血管60多年,91岁院士提醒:高血压除了盐,“3素”也要少吃
- 骨密度|研究显示走路能提高骨密度
- 学术速览|葛根芩连汤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配伍机制
- 为什么肥胖对男性更危险?最新研究揭示背后的生物学机制
- 血液肿瘤MRD动态监测研究及伴随诊断方案(附下载)
-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关于新冠肺炎的研究那么多,这篇儿可能是离咱最近的
- 维生素D|研究发现部分人头晕的原因是缺这种维生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