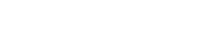文章图片

文章图片

文章图片

文章图片

文章图片
【铜川新区北面,那个叫野狐坡的村子】大人的热闹孩子们从来都觉得兴趣索然 。 他们有自己就地取材的快乐 。 男孩子捡了薄瓦块 , 比赛打水漂 。 打水漂是需要技巧的 , 身体向后倾斜 , 抓瓦片的手臂和水面几乎平行 , 然后向前一冲 , 手用力迅速一甩 , 瓦片擦着水面 , 活像飞碟似的边旋转边从水面上啪啪啪地跳过去 , 霎那间 , 水面上留下了一圈一圈的水纹 。 动作利洒 , 一气呵成 , 弧度漂亮 , 满堂喝彩 。 胜者得意之色在小脸上升起 。 技术不过关的便捡来一堆瓦块 , 憋足了气 , 发誓今天非得练出个渠渠道道来 , 直到巷子里响起家人高声低声的呼唤 , 才悻然离去 。 农村最不缺的就是土 。 七八岁的女孩子则围了一圈 , 和一堆泥 , 头顶着头 , 半跪在地上摔泥泡 。 脸上 。 头发上都沾上了泥点点 , 裤腿子上沾满了土 , 起来 , 随手一拍 。 母亲瞧见了 , 不痛不痒地呵斥一句 , 却依旧我行我素 。 夏天日头暴晒 , 只有鸣蝉在枝间声嘶力竭 。 歇工的大人在阴凉处打盹 , 男孩子们溜出来 , 呼朋唤友 , 去涝池打江水 。 他们一个个赤条条在水中如泥鳅般穿梭 , 有的只露个头 , 给旁边猝不及防的伙伴撩一捧水 , 于是一伙人在嬉闹中漾起一道道水花 , 就如盛开在空中的欢乐 。 每天的热闹都在持续 , 直至池水结成又硬又厚的一大坨冰 , 直至瘦了的村庄被裹上臃肿的厚棉袄 , 那些热闹才被分解到每一个安详的小院:暖暖的热炕头女人们一针一线纳鞋底、收音机里咿咿呀呀的秦腔荡气回肠……
记忆之三编荆芭
村子人口多 , 人们都在土里刨食 , 又处于一个干梁上 , 靠天吃饭 。 收成好 , 家里吃喝凑合 , 收成不好 , 填饱肚子都是问题 。 况且除了一大家子的吃喝拉撒 , 给娃娶媳妇、盖房子 , 家里人有个头痛脑热 , 哪一样不需要钱啊 。 土地贫瘠 , 收入微薄 , 人们便寻思着能搞点副业 , 也好使捉襟见肘的日子稍宽泛一点 。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 村子里青壮年劳力在农闲之余就搞起编织 。 架子车是当时农村最主要的运输工具 , 收麦子、掰包谷、拉粪土 , 少不了拦挡的东西 , 那就是荆芭 。 割草、拾麦穗、揽柴草 , 更少不了笼 。 荆芭和笼的原料后原的山上到处都有 , 就是费些功夫下些苦的问题 , 故乡人有的是吃苦耐劳 。 凌晨三四点钟 , 几个人推着自行车 , 在黑乎乎的巷子里深一脚浅一脚出门 。 后架上 , 夹着磨得锃亮的镰刀和一把细绳 , 车前挂个馒布袋 。 队伍顺着耀柳公路一路呼哧呼哧北上 , 天麻麻亮 , 他们已经站在柳林、瑶曲或者更远地方的山上了 。 密密麻麻细长的各种植物 , 在他们眼里就是最稀罕的东西 。 镰刀的寒光变成一个动作的舞蹈 , 在此起彼伏的咔嚓咔嚓声里 , 一根根荆条脱离母体 , 泛白的茬口丝毫不拖泥带水 。 割好的荆条摆放在一堆 , 觉得差不多了就用细绳困成结实的一大捆 , 自行车后面一边绑一捆 。 回来路上 , 自行车变得无比笨重起来 , 骑在上面 , 身后就像两架摇摇晃晃的小山 。 那时候 , 九里坡的山道上 , 随处都可以看到驮着荆条的人 , 不用说 , 那都是我们野狐坡人 。
荆条割回来放久了太干太硬 , 容易折 , 到时还得淋水 。 趁着韧性刚好 , 立马就进行编织 。 端个小凳院里坐了 , 旁边放置一头用破布包了的刃片 , 平日摇耧使锹拿镢头的粗糙大手 , 此时变得无比灵活起来 。 削、刮、弯、压、手指翻飞 , 荆条在手下如织布的梭子 , 来来回回 , 如此这般 , 不大工夫 , 一张荆笆就编好了 。
- 到过这些地方立即报备!宝坻、滨海新区通告
- 成都市高新区科技创新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小宁一行到访智数医联交流学习
- 浦东新区医学影像高峰论坛举行
- 高新区马金铺街道大营社区、高登社区实施临时管控
- 长春净月高新区:建立林长制 实现林长治 多措并举保护森林生态环境
- 喜报!上海纳诺巴伯荣获「2022浦东新区科技发展基金资助立项」
- 济南高新区:智慧农业助力农民丰收 无人驾驶农机走进农田
- 兴义市义龙新区开展食用菌种植技术培训
- 河南郑州郑东新区、登封市调整部分区域风险等级
- 亳州高新区推进“老有所学”为老年人生活添彩